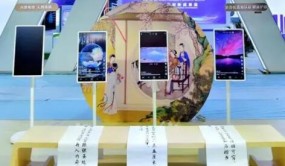环保部发布了《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6)》,我国噪声污染问题已经相对普遍
,1/4的城市基本是“睡”在噪音里。
噪音的研究依然是文化研究学界、地理学界、历史学界的重要话题。早期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多是把噪音当作对专制政权的反抗——对噪音的监控就是对底层的政治压迫。后又有学者超越了噪音研究的阶级范式,主要探索个性与主体性在噪音反应过程中发挥的功能。其后的研究中,各种为人所厌的日常生活中的噪音均可被纳入其中,噪音在此种范式中是被排斥的,它体现出公众对政治权力宣传的恐惧,对商业活动日常化、常态化的厌倦。
而在中国,因抗战和国共内战让生产活动陷于停顿,解放后的人们一度把“噪声当作国民经济复苏的标志而加以歌颂”。继
《广场舞和摇滚乐哪一个是噪音?》
《我们是被恼人的邻居剥夺了享受安静的权利吗?》
的文章之后,今天推出的是“家用电器噪音”问题,
现代家庭已经实现了一种类似“工业化”的改变,家用电器在家中的共鸣甚至“将私家居室变成了交响乐大厅”,在这样的语境中,在手机和电脑上插上耳机成了我们对抗噪音成了我们对抗噪音的工具,然而这却是一种“以一种噪音,对抗另一种噪音”——这些无时不刻不在网络中的电器以永不消歇的噪音宣告其持久的杀伤力与驾驭能力。在邻居噪音、交通噪音及社会生活中其他需要人被动承受的噪音源之外,家庭与工作场所内部、噪音受害者本身也在持续不断地制造、生产噪音。
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全国主要家用电器产品产量的统计数字中,最经常出现的家用电器包括:彩色电视机、组合音响、家用洗衣机、家用吸尘器、家用电冰箱、家用冷柜、家用电风扇、房间空气调节器、家用吸排油烟机、电饭锅、冷热电饮水机、家用电热烘烤器具、微波炉,等等。其中,电脑、手机并未列入家用电器名单。汪民安教授的著作《论家用电器》则将电脑、手机一并拢入,探讨了现代人在使用一些主要家用电器时的各种经验,以此反思我们这个已然与机器密不可分的时代。相较其他家用电器而言,冰箱的工作时间是最长的,但如今,这一“最长”系列又增添了手机和电脑。整体来说,从噪音角度来关注、研究家用电器之负面效应,在中西方都还是更多关注其对身体层面的影响,在文化、心理层面为数不多。
与家用电器共居一室
经医学研究测试证明,住宅内噪声白天不宜超过50分贝,夜间应低于45分贝,如超过60分贝,即会对人的身体与精神产生一定影响。国家环保标准依此对城市五类环境噪声标准做出规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虽然各种家用电器都与科技这个通常被认为是中性的词语相关,很多宅男宅女可凭这些机器足不出户地工作与生活,但如果从其发出的噪音及其对身体的伤害来看,它们均可成为潜在的健康杀手。经过测定,洗衣机所产生的噪音大概在47-71分贝,电冰箱为34-52分贝,电视机可至60-80分贝,电吹风是59-65分贝,甚至小小的电动剃须刀都在47-60分贝。它们各自发出的噪音都有可能超过住宅最低噪音标准,而几种家电共鸣、共振却早已是都市人的生活常态。某种意义上,现代家庭已经实现了一种类似“工业化”的改变,音频系统甚至“将私家居室变成了交响乐大厅”。
如果考虑到家用电器为我们带来的便利性、快捷性与智能化,那么它们在反方面所造成的伤害其实要远远超过其优势,它对人之听力、视觉、心血管、生殖能力、神经系统、精神抑郁等方面的诸多负面影响已经为医学所证实。表面上,家用电器就像人之手的延伸,人通过轻轻按动开关或者点击按钮,机器就可以帮助人完成后续的家务劳动,人由此实现对物质、技术的占有与操控,以及对自我生活的掌控;但是,家用电器在让人产生轻松感、优越感的同时,又以永不消歇的噪音宣告其持久的杀伤力与驾驭能力。可以说,在邻居、社会之外,家庭自身也在持续不断地制造、生产噪音。
这些电器改变了家庭、邻里的声音景观,导致私人空间与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冲突频频涌现。研究表明,家用电器噪声对邻居的影响,主要是靠建筑物传播,而非靠空气传播。卡琳·拜斯特菲尔德在其专著《机械声音》中曾专门考察过由留声机、收音机引发的邻里冲突。有资料记载,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荷兰地方警察参与干预家庭噪音7万次,主要就是基于现代技术工具而产生的邻里噪音;至少三分之一的荷兰人抱怨受到邻里噪音的干扰,而这些噪音大多来自收音机、音响或电视。而如追溯更为久远的年代,那么关于留声机的邻里争执早在20世纪初就已频频发生,以致鹿特丹政府曾经规定,在以下情况要禁止使用“机械乐器”,即在家庭、房屋、厅、建筑物、阳台、门廊、开放附属物等处使用留声机时,只要声音传出所在空间之外,就是不被允许的。但这样的规定随即引发阶级冲突,左翼人士认为,进入20世纪之后,留声机、收音机的价格已经大大下降了,终于成为底层阶级可以消费得起的物质产品,这种小型家电可以让家人或邻居之间感情愈发亲密,如若禁止留声机播放,那对底层阶级的精神文化和尊严是一种严重的损害;而且,如果只禁止留声机的使用,却允许钢琴、管风琴等音乐传播到大街上,那将是非常不公平的。鹿特丹市议会会员则认为,将留声机置于窗前连续播放几个小时而其实根本不听是一种个人的放纵行为,而且音乐家弹奏的音乐与机器制造的音乐有着本质性差别。这种本质性的差别在于前者出自人的强大精神力量与有限的体力,后者则因为源自机器而缺乏人之理性,因其似乎永不疲倦地运转而令人生厌。因此,鹿特丹等地方政府一度规定,禁止连续几个小时播放收音机,只要构成扰民就要对其实施罚款等处理措施。
一定程度上,限制使用收音机与叔本华、鲁迅对噪音发出者的痛恨表现出类似的阶级冲突。通过将不被文化精英接受的品位定性为野蛮,知识阶级有意确立自己的文化资本,提高自己的文化优势。这种思维方式在荷兰一度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不过后来在西方城市对机械音乐的治理过程中又发生了诸多变化。
首先,人们逐渐意识到工人阶级也有欣赏音乐的文化权利,当中产阶级、上流社会去旅游、度假时,工人阶级能享受到的为数不多的精神娱乐就是源自听收音机。第二,当心理学家发现,“噪音同时还是个体心理状态的产物”,因此很难决定哪种声音对哪些人构成干扰时,知识分子将噪音等同于野蛮、将自己与静寂和文化优越等同的精神优势就被瓦解了。诸多事实证明,人对噪音的感觉能力是有巨大差异的,有些人的确比他人更敏感,但是这并不代表其文化或阶层优越性;相反,这种敏感之人经常被看成是个性有问题,或者精神状态过于紧张。第三,一些从事特殊职业者,如铜匠、铁匠、纺织工人、锅炉制造工等听力受损尤为严重,长期从事者甚至会失聪。而且,栖于陋室的底层遭受的邻里噪音之痛绝不亚于身居优雅房舍的中产阶级和贵族。第四,实际上,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敏感的医生就已经意识到了噪音的危害,如果说原先的城市问题主要集中于水、土壤、垃圾或者气味,那么世纪之交,比如说在维也纳,城市问题的“焦点已经转向了噪音”。医学实验证实,噪音会导致呼吸频率与血压上升,并且人对噪音的身体反应及大脑反应都会变慢。医生们还明确提出,“在大城市不断增加的噪音与居民神经问题显著的增长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甚至“神经衰弱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典型病症,因为他们的感官受到噪音的刺激,高度活跃”。噪音因此逐渐被视为所有人的“健康杀手”。
在以上这些因素的多重影响下,西方城市终于意识到不只是机械音乐,实际上所有的音乐、所有令人不悦的声音都可能形成噪音。与此同时,部分城市开始采纳分贝(decibel)概念,寄希望于这种科学的、客观化的数据来对噪音问题进行有效的、有理有据的治理。噪音在此时终于被认为是一种污染,一种公共领域话题,而非单纯的阶级冲突问题,或者说个人生理或心理的敏感度问题。而要治理高噪声强度,首先必须将它测量出来。二战以后,伴随着洗衣机、冰箱、微波炉等更多的家用电器问世,对其声音强度的量化也就成了判定其是否构成噪音污染的重要指标。不过这种数据的所谓客观性、科学性必然要与个体对噪音的感知差异构成矛盾,而这正是噪音纠纷经常要面对的问题。
亲密无间的电器如何剥削我们的生命时间
如果说其他家用电器发出噪音是可以控制的,比如通过关闭按钮直接结束噪音,那么手机因为必须与外界联通——这是手机最本质的性能——而发出的各种声音却是最不可控的(除非完全设置成静音,但手机主人往往很快就将其恢复成正常状态)。它们突如其来,“炸开了既定的平静时空,并且扰乱了先前的平静心情”,与让叔本华备受折磨的街头马鞭声类似,后者也是无法预料的,且“……那样尖厉,那样刺痛人的大脑,使人觉得大脑里有一种灼痛”,叔本华觉得自己的思路“仿佛两腿负重而试图行走那样困难”。手机铃声大概不会让人的大脑产生如此灼痛,但是“意料之外的频繁电话(以及短信),有时候会让人撕裂成一段段的碎片”,听者原本的思路就会因这种撕裂而呈现跳跃性、发散性。对一些商务人士而言,频繁的电话还会造成其事实上的听力受损及免疫力、生育能力受损等病状。时至今日,手机在很多功能上已经取代了电脑,在很多公司白领、教师、学生等使用群体中,以智能手机客户端传送文件的信息交流方式已经比较普遍化。
不过几年时间,智能手机在很多人的身体经验中就已经超越了电脑曾经与人达到的亲密度,也就是说,早晨第一件事由打开电脑变成了打开手机,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则由关闭电脑变成了刷手机。手机可以二十四小时无间断、无距离、无障碍地陪伴我们,丝毫不理会专家对我们苦口婆心的警告。我们似乎很愿意承认:一听到手机各种App的声音,精神就马上振奋了起来。
美国学者乔纳森·克拉里所著的《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刻画了资本主义对睡眠时间、周末时间无孔不入的剥削与占用;由此推延,当手机可以替代电脑从事很多工作时,人们可能就更加需要时时刻刻在工作,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言,“当下的生产空间已不再是工厂,而是城市;剥削的对象也不再是工人的剩余时间,而是人在社会中的生命时间”;也可能时时刻刻在娱乐,手机游戏、购物、聊天、交友均可归为此范畴,这种虚拟的娱乐在某种意义上却是退出城市公共生活的娱乐,是一种囿于“私托邦”(privatopias)的娱乐 。因此,新媒体技术改变了资本主义语境中的工作伦理,工作与生活进一步结合而不是分离,职业文化与日常生活文化混为一体而不是被分割。值得深思的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理论家们曾经将工作与生活之分离视为资本主义的罪恶之一——即造成人的全面“异化”,勤奋劳动的结果不是丰富自我、发展自我,而是造成人的自身否定,人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异己的、与人对立的东西——那么在当下的新媒体时代,工作与生活之界限的跨越与混杂却将是劳动过程中的又一次重大异化。在将劳动时间向着24小时的趋势延长之时,它还对劳动者日常生活中的身体与精神状态带来一种新的暴力伤害。
在此借用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对资本社会的批判,我们就会对此看得非常清晰,“资本不但必须借由它的实现吸收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还必须设法占据新技术释放出来的自由时间”;而现实已经证明,“资本在这方面大获成功”。在哈维看来,从技术上而言,诸如微波炉、洗衣机、烘干机、吸尘器、网络银行等技术和工具——应该也包括手机、电脑,虽然哈维在2014年写作《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之际似乎对新媒体技术还并未格外关注,但他当然注意到了人们“常常无益地连续好几个小时看情景喜剧、在网络上闲逛或是玩计算机游戏”——本来能够帮助人们“倾向抵制支配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建立一个能规避资本主义时间纪律的非资本主义世界。但是,资本却转而让人们将好不容易节省下来的闲暇时间大量消费在家务劳动、社交媒体上;由此,继在生产领域获得剩余价值之外,资本又借助在消费领域制造“众声喧哗”,从而获得大量的资金回报。